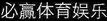规范基金退出管理,拓宽基金退出渠道,建立科学高效的退出机制,对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良性循环、提高财政资金政策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办公厅2024年12月印发的《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优化基金退出机制,推动投资良性循环,为政府投资基金退出提供了系统化政策指引。根据上海投中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的统计,截至2024年,我国政府投资基金累计设立1627只,累计规模达3.35万亿元,2014~2016年成立的大批基金集中进入退出清算期。规范基金退出管理,拓宽基金退出渠道,建立科学高效的退出机制,对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投资—退出—再投资”良性循环、提高财政资金政策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地方政府不断优化政府投资基金退出管理,在主体责任界定、容错机制等方面开展创新实践,探索适合政府投资基金特点的解决方案。例如,山西省财政厅出台《省级政府投资基金退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省财政厅、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机构和母基金管理机构权责,提出通过完善退出程序、让利处理和强化监管,平衡基金政策目标与收益诉求,为财政资金安全退出提供制度保障。
容错机制创新成为各地改革重点。截至2024年,超过20%的地方基金管理办法明确设定容亏量化标准。例如,吉林省提出分阶段风险容忍机制,对科技成果转化中试项目设置80%投资损失容忍上限;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创业母基金允许种子直投、天使直投单项目100%亏损。此类实践与“耐心资本”理念深度契合,通过容忍短期风险换取科技领域的长期突破,缓解基金管理人退出压力。
高容亏率设计可能造成基金风险敞口过大。为此,无锡、广州等地通过出台基金管理办法,以分层容错框架和风险准备金机制平衡基金的局部容错与整体安全。比如,无锡市根据基金类型设定差异化容亏上限,种子基金、创投基金和并购基金分档设定50%、30%和20%的整体容亏上限;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科技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要求按照退出收益的5%计提风险准备金,用于弥补超亏部分。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协同效应显著增强,地方政府投资基金退出模式创新持续深化。北京市、上海市等地已陆续开展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例如,北京股权交易中心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合作,为北京市优质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挂牌加速服务,促进区域性股权市场与更高层次资本市场之间联动。截至2024年底,北京股权交易中心基金份额转让平成基金份额转让和质押140单,实现资金融通规模350亿元。
区域S基金(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平台加速布局。江苏省、安徽省等地国资牵头整合资源设立S基金。江苏省依托区域性股权市场成立S基金联盟,以江苏股权交易中心为主体,吸引民营资本参与S基金,为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提供更加便捷的退出选择。国资主导的合肥市共创接力基金认缴500万元持有苏州上实盛世园丰S基金0.56%的份额,既盘活了存量资产,又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链注入了接续资本,形成国资跨域接力新模式。
政府投资基金作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的一种类型,其运作效能与退出表现深度嵌入私募基金行业生态。2024年,私募基金退出一度陷入“量增质降”的结构性困境,私募基金退出数量同比上涨22.88%,但回笼金额下降9.18%。IPO作为私募基金主要退出渠道,2024年A股首发上市企业仅100家,募集资金673.53亿元,同比分别下降68%与81%;港股、美股市场亦未形成有效替代,IPO总数合计不足百起。在监管层严控发行节奏,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的双重挤压下,私募基金依赖的IPO退出路径实质性收窄。
回购退出陷入两难境地。2024年,因项目破产或经营恶化导致的回购违约案件中,诉讼周期平均长达18个月,且成本回收率不足40%。此外,区域性股权市场流动性不足,且流拍情况较多。
政府投资基金的估值是一项涉及多主体和多层级的复杂工程,其核心挑战源于“母基金—子基—被投项目”的三级穿透结构,以及不同生命周期与技术属性企业价值生成机制的差异。其中,科创企业估值缺乏统一标准,母子基金模式的政府投资基金通常间接持有被投企业较小的份额,企业方出于信息安全方面的考虑,对基金估值尽调的配合度存在不确定性,易造成估值偏差。
管理费设定不合理会影响基金管理人退出动力。政府投资基金普遍采用“管理费与实缴规模挂钩”机制,当市场环境不佳、项目估值下滑时,基金管理人无法通过项目退出获取合理回报,而管理费会随着基金规模的下降而减少,但管理机构仍需要维持团队运营成本,逆向选择效应会导致基金管理人的退出动力不强。
容亏机制执行困难。2024年,全国各省市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中有超过八成纳入尽职免责条款,但多数缺乏配套的责任认定细则,而且分阶段容错机制可能存在执行僵化风险,易引发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bwin官网
政府投资基金的跨周期、跨地域资源配置职能与基金属地化管理形成矛盾。一方面,跨区域股权及份额转让需履行属地审批程序。目前已经出现在国资S基金与另一地区政府投资基金拟开展股权转让时,转让方受制于对“属地化国有资产”转移可能触发监管争议的担忧而主动终止交易的情况;另一方面,缺乏针对政府投资基金的估值标准,进一步影响了流动性。在以上两方面因素作用下,2024年政府投资基金份额转让事件中44.4%交易对手方为关联投资者,即其与基金在股权结构或控制关系上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民营资本等体系外资金因制度摩擦与估值风险选择“用脚投票”,政府投资基金退出“内循环”情况较为严重。
为拓宽退出渠道,建议各省推动省级S基金布局,将并购基金纳入产业规划。一方面,积极推动建立省级S基金与区域性股权市场的联动机制,通过标准化交易流程、合格投资者定向撮合、第三方评估机构库建设等创新,形成“数据支撑估值—平台撮合交易”闭环;另一方面,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细分领域,积极设立并购重组基金,通过省级“S基金+并购基金”模式,激活产业链横纵整合效能,提高资本市场活跃度和资源配置效率。
为提升区域性股权市场流动性,建议在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试点估值规则互认机制,并将估值报告上链存证,允许经第三方审计和监管部门签字的上链估值报告跨域采信,降低交易合规成本。积极推动投贷联动,吸引银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险资参与政府投资基金股权交易。
针对科创企业技术迭代快、无形资产占比高的特点,建议构建分类估值框架。对于早期项目,可在估值模型中加入技术成熟度系数;在项目成长阶段,可以引入实物期权法等方法进行估值;在项目成熟期,则可以采用收益法与市场法交叉验证。建议政府部门出台政府投资基金投资标的估值政策指引,从母基金、子基金和底层项目三个层面规范估值流程,推进政府投资基金估值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积极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开发智能化估值平台,整合子基金和企业的财务数据、可比上市公司数据、专利转化率等指标,为交易双方提供较为精准的估值参考。
各省级基金主管部门应统一退出程序与监管标准,细化强制退出和到期退出条件。为压实基金管理人责任,建议在合伙协议中明确基金退出条件、退出时间、退出方案编制要求等,将退出进度指标与管理费兑付阶梯式挂钩。主管部门应制定尽职合规免责实施细则,建立过渡期观察和整改约谈等缓冲机制,逐步规范容错免责程序,健全基金管理机制。
分阶段容错机制需根据项目类型进行动态调整。对硬科技类项目,容错率应与研发阶段达成率相关联,在达成阶段性研发目标后,应动态调整后续资金支持力度和项目容错率。对模式创新类项目,应从严控制,防止基金管理人道德风险。考虑到政府投资基金的政策属性,在退出管理机制中应审慎实施排名淘汰机制,对非主观因素或不可抗力导致的退出延迟,要实施分类考核。■